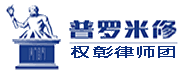论行贿罪排除性规定中“被勒索”情节的认定标准
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 冯冰扬
在行贿犯罪辩护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称其系被公职人员采取威胁、刁难或“哭穷”等方式索贿,而不会承认其主动行贿:“是他主动向我要的钱,我怕不给生意就不好做了,我是被迫的”“他主动要钱,我觉得给钱能更好地维系我们的关系,方便未来业务的开展,就算以后查起来也能说不是我主动行贿的”。刑法在行贿罪规定中确实对被索贿情形作了排除性特别规定,但对于“被索贿”情节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较大分歧。

作者:冯冰扬
一、刑法中与“索贿”有关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3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此即行贿罪的排除性规定,或称为行贿罪的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基于此规定,同时满足“被索贿”和“未获得不正当利益”条件的,其行为不是行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和可谴责性,不构成犯罪。
从上述条文可知,虽然行贿罪和受贿罪法律规定中均提及了“索贿”的情形,但并未对“索贿”的定义作出详细说明,由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构成要件在认定标准上存在分歧与争议。
二、“被索贿”情节认定标准的争议焦点
(一)行贿罪中的“被索贿”与受贿罪中的“索贿”是否存在对应关系
根据上述刑法条文可知,行贿罪和受贿罪中对“索贿”“被索贿”的描述存在细微的差别,受贿罪规定中直接表述为“索取他人财物”,而行贿罪规定中则描述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从文义上看,“索取”一词指要求得到,其核心特征在于行为的主动性,而对于行为的强制力未作要求;“勒索”一词则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迫使被害人处分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行为对被害人的强制性。
据此,有观点认为行贿罪中的“被勒索”与受贿罪中的“索贿”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应严格遵照文义解释,只有导致对方迫于心理强制而违背自身意愿处分财物才是行贿罪中的“被勒索”。简言之,这种观点是把行贿罪中的“被勒索”和敲诈勒索罪中的“勒索”做同一理解的。
相反观点则认为,行贿罪中的“被勒索”须对应受贿罪中的“索贿”进行理解,其含义就是指索取,不应当在索取的基础上另外附加其他条件。(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1页)
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能兼顾立法本意和社会治理客观需要,理由如下:
第一,行贿罪与受贿罪属于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即二人以上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如果对于对向犯在同一犯罪构成要素的认定上采取明显不同的标准,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受贿人构成索贿,而行贿人却不构成被索贿),法秩序的统一性会受到破坏。
第二,将行贿罪中的“勒索”对应理解为受贿罪中的“索取”,并未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属于限缩解释,并非刑法所禁止的类推解释。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中一切解释方法的基础,任何解释都不应过分脱离条文的基本文义,否则将构成刑法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绝不能仅囿于文义而作出僵化、教条的解释,否则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刑法将难以发挥其规制行为、保护法益、保障人权的机能。在不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适当对文义进行限缩或扩张,可以使其更加符合立法本意、更加贴合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
第三,将行贿罪中的“勒索”对应理解为受贿罪中的“索取”,更符合打击贿赂犯罪的治理策略和立法目的。行贿与受贿往往是暗箱操作,双方都有利可图,且一旦败露又都要治罪,所以行贿人与受贿人往往心照不宣,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如果立法上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行为,那么,受贿人惧怕被告发而不敢受贿,行贿人惧怕人家不收受而不敢行贿,双方处在囚徒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贿赂的发生。(参见张明楷:《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刊登于《法学家茶座》,2004年第5辑)因此从宽认定“被勒索”,将其对应理解为受贿罪中的“索取”,能够扩大行贿人出罪的空间,鼓励行贿人积极举报受贿对象。2023年发布,2024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将行贿罪的基础刑期适当下调,此即通过立法形式对上述观点予以肯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贿罪第三款排除性规定中的“被勒索”和受贿罪中的“索取贿赂”属于一一对应关系,只要受贿人的行为属于索贿,那么“行贿人”就属于“被勒索”。
(二)什么是“索取贿赂”认定标准的核心
结合上文,笔者认为行贿罪中的“被勒索”与受贿罪中的“索取”属于对应关系,二者应适用同一认定标准,只要受贿人的行为属于索取贿赂,那么“行贿人”就属于“被勒索”。在此基础上,还需把握住“索贿”认定标准的核心,才能对行贿罪和受贿罪这一对向共同犯罪作出公平合理的裁判。
有观点认为,认定行为属于索贿的核心在于该行为对于相对人具有强制力,使相对人迫于受到的心理强制而违背自身意愿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在这种观点下,由哪一方率先提起贿赂的事宜并不重要,即使是行贿人主动提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一定的钱财,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借此“狮子大开口”,强制要求行贿人给予超出其预期财物的,也能构成索贿。(2018)粤01刑初510号判决书、(2021)青0122刑初329号判决书及《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431号——吴仕宝受贿案等裁判案例中,人民法院即以这一观点作为裁判依据,认定只有对相对人造成心理强制,迫使其违背自身意愿处分财物的即构成索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定行为属于索贿的核心在于其主动性,行为是否对相对人造成强制在所不问。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人的“索要”可以体现为以各种形式平和地主动索取,也可以是带有“勒索性”的索取。即不考虑行为人的索贿行为是否带有强制性、是否对行贿方产生强迫与压制以及行贿方的心理状态,只要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在行贿人表示给予财物之前主动索取并接受了财物,便构成索贿。对于这一观点,存在较多的裁判案例作为支持,如(2023)青0103刑初305号判决书、(2014)湘高法刑二终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2013)鄂刑二抗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2017)苏刑终48号判决书、(2017)吉刑终163号判决书、(2019)湘0991刑初47号判决书、(2018)赣0726刑初56号判决书等。
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理由如下:
第一,在索贿行为达到了使相对人迫于受到的心理强制而违背自身意愿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程度,即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勒索程度时,所谓的“行贿人”实际上变成了犯罪的受害人,此时当然不属于行贿,在立法上根本没有必要单独设立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排除性规定。
第二,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要构成行贿罪,除了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以外,还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第三款的排除性规定则认定被勒索且未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犯罪。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本来就不构成行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的排除性规定并非通过法律拟制将本应构成行贿罪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以外,而是通过这一注意性规定,对不符合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而不构成行贿罪的行为加以强调。即判断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仅凭其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即可得出结论,在此前提下第三款中“被勒索”情节的含义应外延为“索取”,只要行为人先向他人表现出索取财物的意思,其行为已经构成索贿,而不必再去讨论其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甚至是暴力性。
第三,后一种观点更能体现刑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本意、更符合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贪污贿赂犯罪所共同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索贿行为结合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无疑应受到刑法的重点约束,因此刑法在受贿罪条文中专门规定了索贿的情形,对其适用较为宽松的犯罪构成要件,同时规定对其应从重处罚。行贿罪作为受贿罪的对向共同犯罪,为保证法秩序的统一性,也应采取相同的法律适用标准,因此从宽认定“被勒索”,将其对应理解为受贿罪中的“索取”,能够扩大行贿人出罪的空间,鼓励行贿人积极举报受贿对象。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行贿罪第三款排除性规定中“被索贿”情节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均有相应判例予以支持。笔者认为,行贿罪中“被索贿”情节的认定标准应与受贿罪中对“索取贿赂”的认定相对应,只要受贿人的行为属于“索取贿赂”,那么“行贿人”就属于“被勒索”;对“索取贿赂”的认定,应以索贿人行为的主动性为核心。通过这样的认定,能够扩大行贿人出罪的空间,一方面有利于鼓励行贿人积极举报受贿对象,使得行贿受贿双方都处在囚徒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避免将一些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
若您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欢迎来电咨询400-057-3132或者13530053568(微信同号)普罗权彰律师团包含有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成立以来经手案件上千起,均取得满意结果。
品牌律所,超过500名执业律师、专家、顾问、专业人员,全国多家分所☞律所最新资讯

普罗权彰律师团队包含有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团队,该团队在刑事辩护领域,辩护经验极为丰富,有为多位犯罪嫌疑人成功办理无罪辩护、取保候审、罪轻辩护、减刑缓刑的案例,深得委托家属一致好评。该团队为深圳市第一看守所、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深圳市第三看守所、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深圳市龙岗区看守所、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深圳市盐田看守所关押人员专业办理刑事辩护,普及刑事案件相关知识。